荷兰纪行(三)
夏天逝去,气温走低,密布的层积云爬上了天空,漫长风雨季将至的阴郁感受让人回忆起种种不快。不过今天路上遇到一个荷兰小孩儿冲我招手微笑,也算是在我心中投下了一缕希望的微光。在来到荷兰正满一年之际,我要好好吐槽一下2022以来的不幸,也期盼一切都能好起来。
荷兰医疗系统深度体验官
这是我前段时间在一个朋友的群聊里获得的群头衔。故事要从漫漫长夜下的深冬讲起。那时刚进入2022年没几天,高纬度的荷兰在下午四点多就开始天黑了。看着外面五点钟就已如同深夜的街道,我像往常一样鼓起勇气踏出房门迎接阴雨:菜又吃完了,得去买了。当时的我还不知道,三年前的梦魇即将再次登门。刚一出来,右肩背部就传来一阵刺痛。我以为是太冷没及时穿衣服导致的什么随机反应,没有在意。还在超市买了一提瓶装水用右手提着心想这也没啥事儿。过了几天,一个右胸的怪异症状加重了我的疑虑:在弯腰的时候胸腔内会传来奇怪的声音。我开始担心是最坏的情况发生,但又觉得可能只是什么肌肉拉伤。随后骑车跑去全科医生那里看病,这个代班的年轻全科医生显然没什么经验,拿听诊器听了半天也无法确定是怎么回事,开了第二天在某医院的X光检查。我依旧心存侥幸,还飙车骑回家。直到躺下睡觉时,那熟悉的胸闷袭来,让人难以入睡,我才不得已在深夜来到医院急症。X光显示,右侧气胸复发。
我大概是那种比较迟钝的人,在遇到大事,难事的时候,通常最开始没有什么感觉。或许这是一种应激保护机制,在强烈的变故面前,一切情绪都会被下意识地压抑。就如2018年的第一次气胸一样,当时的我憨憨地在急诊室里躺着,大脑放空,有女朋友陪伴倒也没那么可怕。可如今没有家人也没有好友,舍友把我送到医院门口就回去了,我竟然完全没有思考住院的大小事情。倒是有一种,“啊,终于还是来了”的安定感。
之所以说是“终于来了”,是因为对于我这种原发性气胸,不做手术的话复发率非常高。2018年住院后拍了CT,医生说我的肺部有不正常的薄弱组织,易发气胸,文献报告复发率最高有百分之六十,在瘦高男性中最为常见。我当时没有选择手术,而是希望能侥幸避免复发。我还真是一直心存侥幸啊。就这样苟且了三年多,在我已几乎要忘记此事时,它又来了,如同墨菲定律一般。实话说我来荷兰之前就曾想过,在荷兰复发怎么办。当时我安慰自己,荷兰的医疗水平它还能比中国差吗,大不了我就在荷兰做手术。但是我千算万算,没有算到我复发后又一次拒绝了手术。
荷兰的医生两次三番建议手术,因为手术可以降低复发率到百分之五以内,我也计划趁机了结此事。但是我却遭到家人的劝阻。总之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,我没有手术,而是希望在三月份的时候回国去北京找个好医院做。但是出院没多久,我就又心存侥幸了,决定继续在荷兰待一年直到毕业再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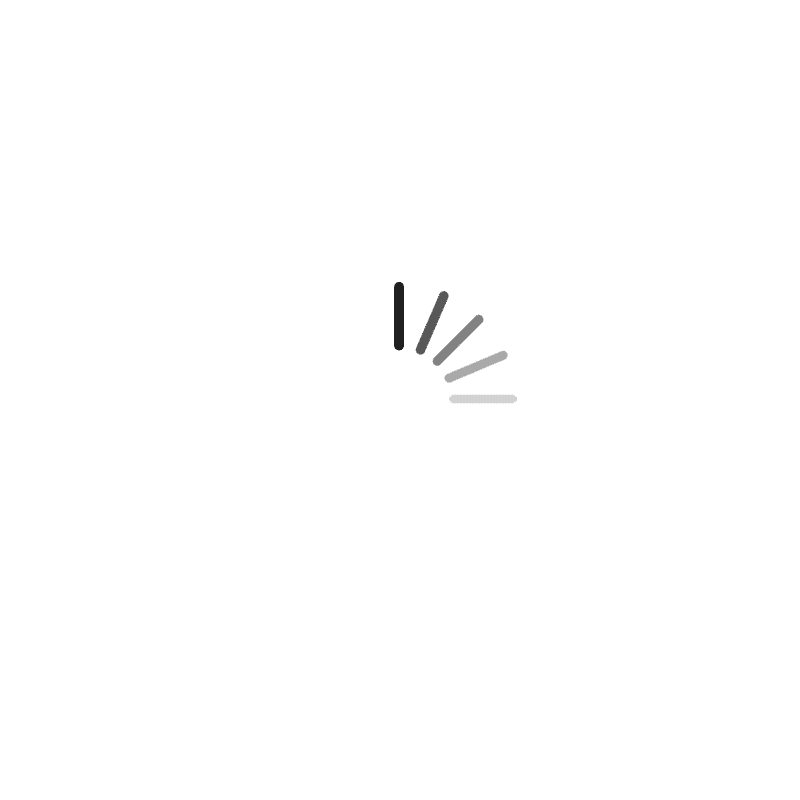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过的飞快,转眼到了五月(中间还得了一次新冠),欧洲人纷纷出游。我也按捺不住,约了德国的朋友去旅行。出发前一周的一个晚上,我躺在床上想,希望这次又是坐飞机,又是出门玩,气胸千万别复发。结果第二天,真的就是第二天,它又来了。因为不想花钱打车,叫了救护车,结果事后收到800欧元的账单,还得自己找保险公司报销。机票和住宿的钱也打了水漂,好在我是穷游,都不怎么贵。
又一次住了院,又一次见到了那个医生,我当即表示要做手术。医生点头微笑,表示同意。一周后我终于做了传说中的胸膜剥离和肺大疱切除手术。全麻时还是一如既往的光速失去意识,要是每天晚上都能像那样睡着该多好啊!总之外科医生说手术很顺利(也无从知晓真假),三天后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出院。胸前插着手指粗的引流管,床头挂着尿袋,就这样又在床上度过了煎熬的三天,我回家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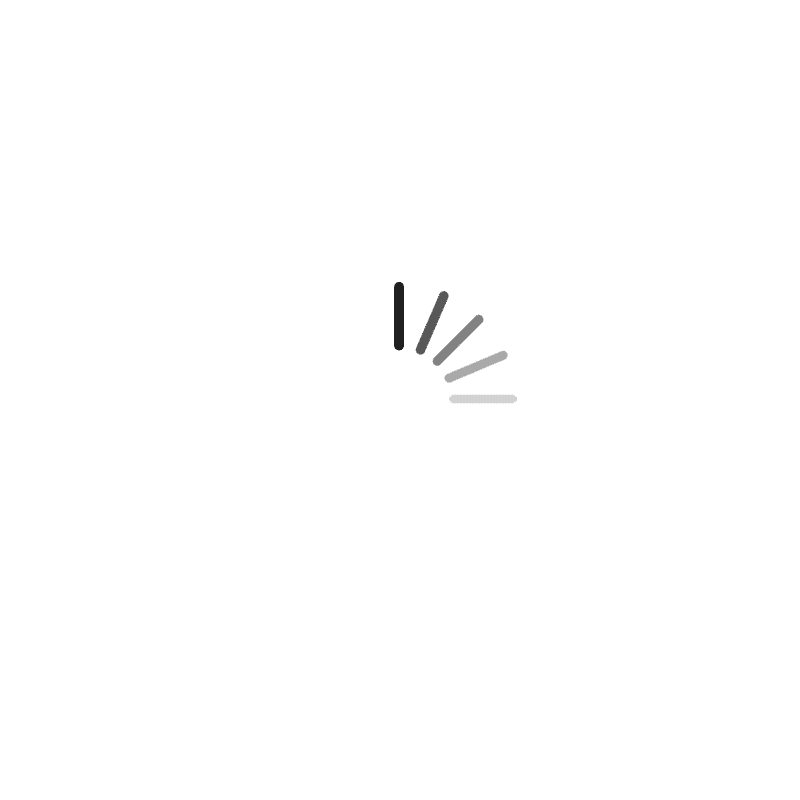
手术后的恢复比我预料的要慢得多,乏力和气短是恢复期的主要不适。整整一个月后我才觉得整个人回到了满血状态。除此之外,因为胸腔镜毕竟还是有创的,我胸前至今还有一块皮肤没有知觉。这种神经的创伤可能要数年才能恢复,甚至也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到最初的状态。不过相比起手术的收益,这算是小问题了。
其实这期间还有各种不顺和疼痛我没有写下来,一方面是过于繁杂,另一方面是写到这里我已不想去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。于是乎我更加钦佩弦子和Jingyao。在博客里回忆住院的经历都足以让我觉得难过与不适,况且在医院我还有止痛药,生病了也不会有人指责攻击我。而她们却要在一次次的起诉与上诉中反复面对过去,还要接受无数双眼睛的凝视。罗翔说他认为勇敢是最稀缺的美德,希望我今后也能像弦子和Jingyao那样,多一分勇敢,少一分怯懦。